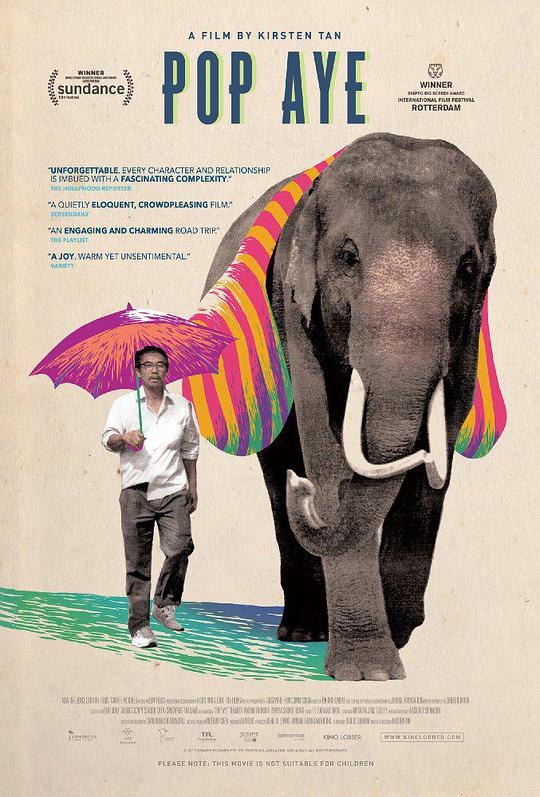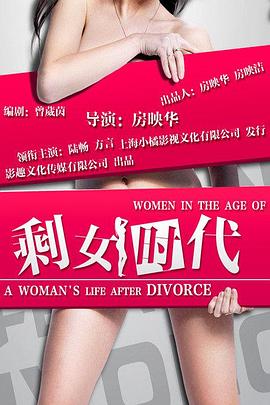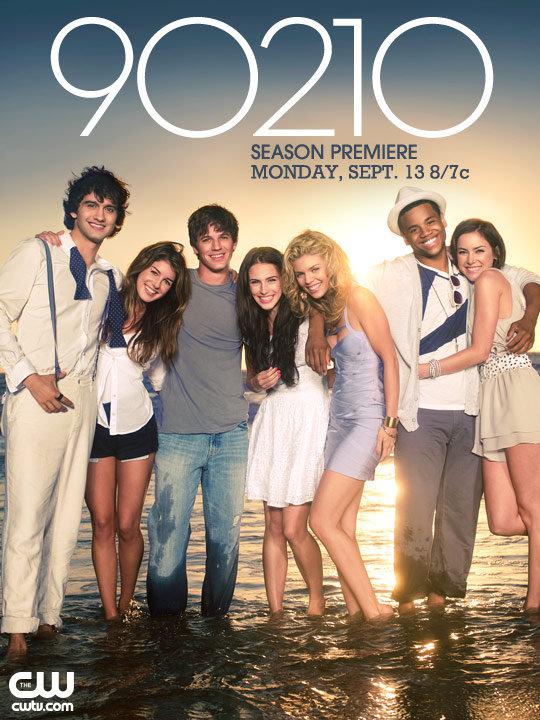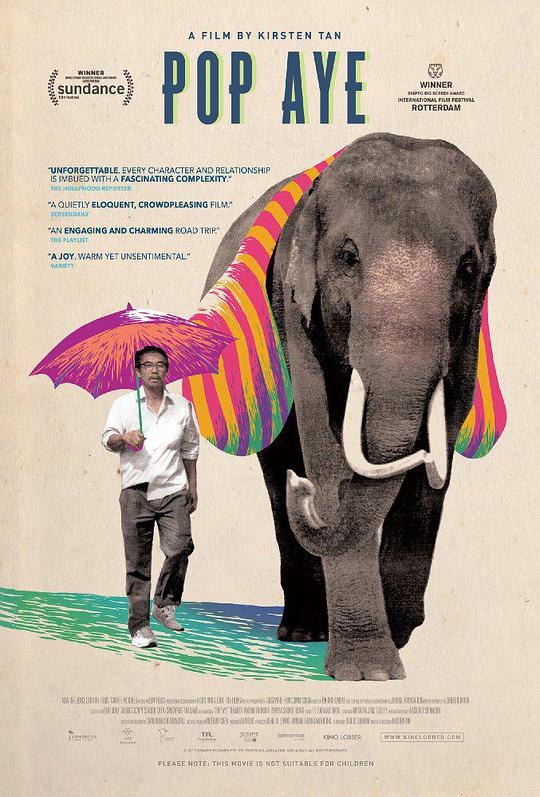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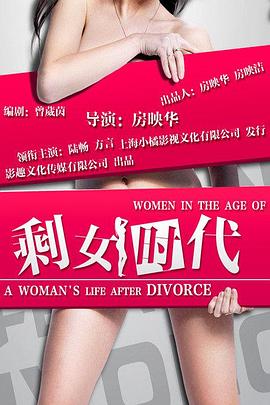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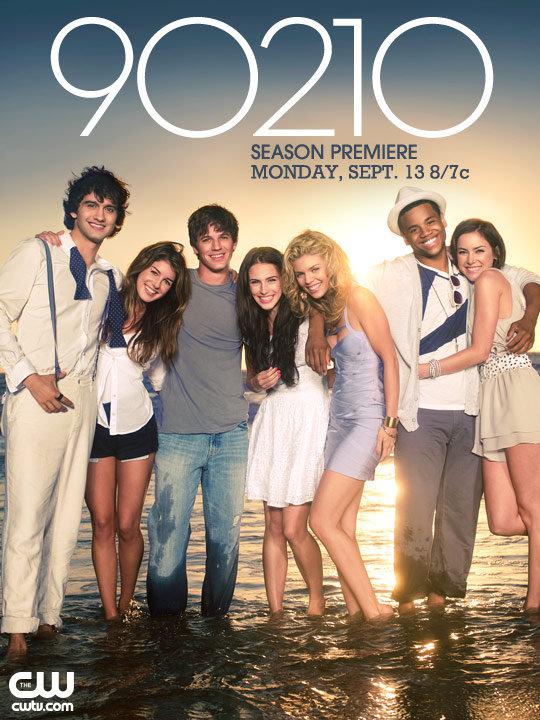
















人工智能正重塑全球的劳动力市场,这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问题是:这种重塑对人类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就业替代与创造能同时到来吗?当AI可以轻松输出海量知识,人类的工作价值要去哪里寻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在其新著《中国就业新趋势——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中,试图找到这些日益逼近现实问题的答案。近日,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人类与人工智能竞争就业的过程中,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与AI的差异化互补。
蔡昉 图/受访者提供
“人类唯一出路是找到比较优势”
《中国新闻周刊》: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哪些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面向未来,这种就业的替代是否会愈演愈烈,我们要如何应对?
蔡昉: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生成式AI的出现,对就业市场已造成显著冲击。美国有调查显示,ChatGPT诞生后,部分白领岗位受冲击明显,尤其是针对新毕业生的需求大幅减少。例如在法律行业,刚毕业的法学生通常负责文案、查卷宗等基础工作,这些恰恰是AI具备高生产率的领域。
实际上,这一轮人工智能引领下的技术革命,与过去几轮不太一样。过去,新技术带来的岗位替代主要针对重复性体力劳动或低技能的半熟练劳动,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却可以替代需要高等教育背景的技术性工作。因此,对很多有技术门槛的行业而言,AI目前也能达到中等熟练程度,入门水平的毕业生容易被取代。未来,随着AI从大语言模型向具身智能进一步发展,更多岗位将面临被替代的风险。
生成式AI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强大的认知能力,在这一维度,其智能水平已超越人类,因此,人类唯一的出路是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与AI在就业市场上形成差异化互补,而非在AI擅长的领域与它竞争,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人机协作与共存。
机器人学者汉斯·莫拉维克曾提出过著名的“莫拉维克悖论”:他发现,对人类来说非常困难的任务,比如成为围棋世界冠军,AI可以驾轻就熟,但人类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比如绕过桌椅把一杯水端给别人,AI却难以模仿。这启示我们,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具有某种不共通性,人类作为一种独特的生命体与智慧体,在进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难以言传的“隐性知识”或“实践智慧”,这些都是更加“人性化”的能力。
这些能力只可意会,却构成了我们的独特性,比如自我控制、团队精神、社交技能以及艺术感知,只有人类才会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而流泪,AI则不会。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人类这些潜在的“本能力量”,放大可以与AI互补的人力资本,这是未来劳动力市场中人机共存的关键。
在人机共存的场景中,工作不应仅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岗位,人工智能可以将传统工作的不同任务分解,重塑整个生产流程,让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负责各自擅长的部分。也就是说,人机协作的新业态中,有机会创造就业的更多可能性。
必须认识到,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破坏就业的同时,也能创造就业。我们应对AI就业冲击时,最核心的策略就是努力让就业创造大于就业破坏,这指向了AI对齐的重要性。所谓“对齐”,就是让AI的发展“为人类所用”,符合人类的目标、偏好及伦理原则。这不仅要在技术模型层面做到,更需要技术开发者、投资者、企业家和用户等多方达成共识,在AI发展过程中确定共同的取向与行动优先级。
10月15日,北京一家视频创作软件公司的负责人用手机展示其平台生成的短片内容。图/视觉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要想实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互补,从人力资本培养的角度,我们的教育应如何革新?
蔡昉: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使得以增加受教育年限为目标的人力资本培养模式日渐捉襟见肘。新的人力资本培养,不能将赌注完全押在学校教育上,必须转向可持续的、贯穿职业生涯的培养,跨越劳动者的全生命周期:一是更加重视婴幼儿早期发展;二是把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都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向前、向后延伸;三是强化终身学习机制。
特别是学前教育。刚出生的孩子会比成人保留更多人类的“本能”,而成年后的人反而更像人工智能。根据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的研究,在婴幼儿0—3岁,对于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效果最为显著,这些对一生至关重要的能力和技能,主要是在儿童期形成。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重心前移,目的不是传授更多学科性知识,而是提高孩子全方位感知世界的能力,让他们学着去辨识事物、判断色彩……这些早期体验非常重要。政府下一步要深度整合学前教育资源,因为越是在较早的教育阶段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越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建立这样一套全周期的人力资本培养体系,核心难点在于如何有效统筹资源。例如,0—3岁和3—6岁儿童在管理服务上分别归属卫健系统和教育系统,这增加了学前教育资源整合的复杂性。事实上,如何处理好每个教育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效衔接,是我国教育体系长期存在的短板。而按照未来人力资本对终身学习的需求,政府可能需要对各个阶段现有的制度安排、教学内容、追求目标和评价手段等进行全面更新。
另外,由于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长期来看,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高中的在学人数会递次减少,使大量教育资源出现闲置,这恰恰为资源统筹与整合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政府可以考虑将部分闲置资源转向职业培训,或者为更多大龄劳动者提供技能提升服务。总之,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培养的人才应具备哪些能力。
2024年4月11日,江苏昆山开发区人社行政服务大厅的办事人员使用“AI 小昆”。图/视觉中国
对AI征税
《中国新闻周刊》:站在政府角度,要想实现对劳动者全生命周期的培训,除了资源统筹外,还需要投入更多财政资金。目前,我国仍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这笔钱从哪儿来?政策层面如何准备好应对AI对劳动力市场的短期震荡?
蔡昉:从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短期影响看,就业破坏总是发生在就业创造之前。研究发现,因技术变革而失去岗位的人与获得岗位的人之间存在明显时差,有时甚至需要通过一代人的更替才会改变职业结构。因此,直面冲击的当下,政府必须为每个岗位被破坏的个体,提供有效的兜底保障机制,这也是一种“对齐”。
在那些实现大规模AI就业替代的行业,未来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引入人工智能税,并将税收所得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用于给受AI影响的劳动者进行转岗补偿、技能培训等各类转型所需的保障性经费,从而缓解技术替代带来的社会冲击。某种意义上,在人工智能时代,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保障性制度应变得更加普惠,政府未来应为所有年龄段的劳动者提供终身教育与培训服务,并承担相应投入。
对AI征税的逻辑在于,如果人工智能的应用真能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给有关企业创造持续的经济价值,生产率提升的红利就不应由个别企业独享,政府应通过二次分配将红利在全社会共享,这需要精细的制度安排。生产率分享机制,一方面可以减少垄断和“赢者通吃”,美国目前已出现这样的局面;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因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给经济结构稳定性带来的伤害。
凯恩斯在1930年曾预言,100年后,劳动生产率必将提高4—8倍,以至于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不用再把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浪费在枯燥无味的工作上。很多经济学家的测算表明,凯恩斯预言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已实现,但今天,人们每周仍需工作40小时,而非15小时,“内卷”背后的深层逻辑,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认为,随着AI带来劳动生产率的飞跃式提高,我们亟须重新定义工作,重构报酬与工作之间的关系。
如果向更远期的未来展望,特别是当通用人工智能(AGI)真正到来后,未来职业应聚焦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届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可以打破资源约束,使人力资本回报与劳动生产率脱钩,尽管这一过程可能漫长,但人工智能比过去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更接近实现这一突破。
以“一老一小”为重点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绕不开当前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当前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具体到“一老一小”,你有何针对性的建议?
蔡昉: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虽已逐步走出疫情期间的周期性失业,但常态化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仍然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具体表现为“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两种现象并存,年轻人群体中流行的“内卷”与“躺平”都是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外显。矛盾的核心原因是劳动者技能与市场需求之间无法形成有效匹配。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实际上弱化了我们应对AI就业危机时的能力。
要想解决就业矛盾,必须以“一老一小”为重点。青年劳动者群体的核心弱势,源自人工智能对入门级岗位的显著冲击,因此,政策设计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强培训,并利用AI赋能,让青年劳动者迅速跨越经验壁垒,将人力资本尽快提升至中等水平。
大龄劳动者面临的就业挑战,不仅是技能过时,还有可能被排斥于整个智能工作环境之外,从而加剧“数字鸿沟”导致的弱势地位。因此,针对老年人的就业支持,除了技能培训,更应强调让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具备辅助性和包容性,也可以设计一些倾斜性的技术方案。
随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未来在劳动者中的比例将持续攀升,提高其实际劳动参与率尤为关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共培训资源应向其倾斜,并通过精准的技能评估,帮助他们识别自身技能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从而进行针对性提升。因此,应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关键,在于推动人口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三者进行深度融合。
发于2025.12.15总第121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蔡昉:AI时代,如何应对就业危机?
记者:霍思伊(huosiyi@chinanews.com.cn)
编辑:杜玮